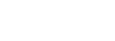《艺术广角》2023年第4期:李鑫艺 | 戏曲中的“醉境”

提起戏曲中的“醉”,所关联的剧目比比皆是,如《贵妃醉酒》《太白醉写》《醉皂》《醉打山门》等。这类剧目中主人公因喜、因愤、因悲、因愁,借“酒力”助燃内心情感的迸发,以“歌舞”演绎思绪翻腾的激荡。酒作为生活中常见的饮品,在戏曲舞台上隐去了其本质的形态,以酒杯、酒斗、酒壶或酒坛这些道具来表意,同时又因“以酒代餐”或“以酒代席”,延伸了酒在舞台上虚拟性的表现,放大了酒对于情与物、人与人,乃至人与神之间沟通的媒介作用,兼具礼的表达及情感的催化。
在一些戏曲剧目中,饮酒往往被当作重要事件或矛盾冲突的发端。戏中饮酒既有积极的一面,可以酒壮英雄胆,让武松醉打猛虎、醉打蒋门神;也有因酒误事,甚至误国的负面渲染,让刘秀误斩了功臣,让张飞丢掉了性命。这些人物有的是在酒力的加持下作出激动之举,有的是因贪杯而变得昏聩无能。

李鑫艺主演的《酒楼》剧照
从古至今,人对于酒的情感依赖是非常深厚的,这自然也包括西方世界的人。古希腊悲剧便是源于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庆典活动。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写道:“或者由所有原始人群和民族的颂诗里都说到那种麻醉饮料的威力,或者在春日熠熠照临万物欣欣向荣的季节,酒神的激情就苏醒了,随着这种激情的高涨,主观逐渐化入浑然忘我之境。”[1]他认为狄俄尼索斯所化身的酒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表示个体情欲的放纵,同时“醉”也可以比拟为酒神的本质。人们在酒神的影响下,载歌载舞,纵情欢乐,释放自己最为原始的本能。而处于东方世界的华夏民族则更多的是将这种情感寄托于诗词中:因喜如《诗经》所云“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因愤如杜甫所吟“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因悲如李清照所作“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因愁成诗的表达是最为丰富的,仅李白一人的诗就不胜枚举,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等。“愁”字似乎成为“太白斗酒诗百篇”的佐肴,诗人有愁便把酒,把酒便伤情,伤情便成诗。
人与酒、醉与愁,古来今往,除却诗,在戏台上更别有一番滋味“却上心头”。恰恰正是这一番愁滋味,引得观众沉醉其中,欣赏剧中人因愁而醉之后呈现出的醉境之美。
醉而生美
戏曲的表演手段无外乎唱、念、做、打四功,演员依靠手、眼、身、法、步的程式技艺来塑造人物形象。人在酒后的情绪波动,恰好为戏曲这一诗、乐、舞高度融合的艺术表现方式带来了发挥的空间。《弟子规》写道:“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最为丑。”但在戏曲舞台上,醉态却是需要用美的方式来呈现的。
京剧《贵妃醉酒》中,梅兰芳先生所塑造的杨玉环自听到高力士、裴力士奏到“万岁爷驾转西宫”之后,一句“且自由他”便开始妒火中烧,以酒消愁,来排遣心中的怨气。从黎民百姓所造的“太平酒”到三宫六院所造的“龙凤酒”,再从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的“通宵酒”直到“换大杯伺候”,每一种酒名看似都承载着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寓意,但在杨玉环的心里却是一杯杯五味杂陈的苦酒。正所谓酒力不可久,愁根无可医,饮到后来“只落得冷清清独自回宫去也”。在这一过程中,杨玉环的醉态在眼神、手势、脚步及舞台调度等方面,都是极具美感的。在脱了凤衣之后,两次闻花的表演,利用“卧云儿”的身段,让观众仿佛看到一位醉卧花中眠的美人。这之后,裴力士、高力士进酒,杨玉环踏步“衔杯”。梅兰芳运用“鹞子翻身”的技巧,控制身体缓慢下腰,一气呵成地将酒杯又置于托盘上,以此表现出杨玉环酒兴正浓,难以自持的意象,让观众在欣赏到美感的同时无不感慨其深厚的艺术功底。对于醉酒后的步态,梅兰芳说:“醉步是怎样走的呢?我顺便也来讲一讲。演员的头部微微晃摇,身体左右摆动,表示醉人站立不稳的形态。譬如你要往右走,那你的左脚先往右迈过去,右脚跟着也往右迈一步。往左走,也是这个走法。还要把重心放在脚尖,才能显得身轻、脚浮。但是也要做得适可而止,如果脑袋乱晃、身体乱摇,观众看了反而讨厌。因为我们表演的是剧中的女子在台上的醉态,万不能忽略了‘美’的条件的。”[2]所以,我们看到舞台上的杨玉环虽因愁而醉,却醉中见美。既美在整体,又美在精微,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恰如其分地营造出戏曲艺术独有的醉境之美。
醉而忘形
古人云:“发于中必形于外。”戏曲表演的内心体验是基于生活的真实,但“形于外”的表现过程是要经过“变形”的,著名戏剧导演阿甲曾把这种“变形”形象地称为“把米酿成酒”[3]。生活是米,戏曲艺术的表演是酒,从米到酒的质变与升华,所需要的是表演对于意象的提炼,从而得其意而忘其形。朱文相、王永庆《戏曲的双重体验与双重表现》一文曾这样说道:“戏曲是以程式的语汇和程式化的语法进行构思设计的思维。它除了同样要对生活本身有深邃的认识和深刻的体验以外,还要把这种认识和体验转化为一种既沉潜于认识和体验之中,又幻化在技艺之外的‘歌舞生活’。”[4]所以,在“醉”的表现上,戏曲最为核心的技术手段——歌与舞,是最能够立象以尽意的。直白地来讲,观众看的就是演员如何在台上运用歌舞来表现人物“耍酒疯”。
比如在昆曲《长生殿·疑谶》中,身中武举的郭子仪徘徊于长安酒楼之中,以酒消遣心中的苦闷。虽然正值青春,意气风发,但他没有像孟郊得中进士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那样放荡不羁,而是胸怀天下,痛感朝政荒驰,报国壮志难酬,因此借酒抒怀。当在酒楼上看到权臣安禄山招摇过市时,郭子仪心中的满腔怨气难以抑制,借着酒劲指着楼下痛骂“乱天下者,必是此人也”。此时曲牌的节奏顿时激切起来,曲调赶板剁字,表现出郭子仪看到安禄山后的愤恨,以及对朝臣中的宵小之辈的深恶痛绝。在表演上,郭子仪将椅子推倒,脚踩在椅子腿上,继而转身一边唱着“定与那私门贵戚一例逞妖狐”,一边横场快搓步。之后更是一边痛饮,一边拔剑作歌“便教俺倾千盏饮尽百壶,怎把这重沉沉一个愁担儿消除”。郭子仪将一坛酒饮下之后,舞起一套“醉剑”。在上下翻飞的剑花里,在快而不乱的招式中,随着锣鼓的烘托,观众看到的早已不是一个醉汉在酒楼里“耍酒疯”,而是这位日后“百战兴中唐”的郭子仪,在醉乡中手执利刃对着祸国殃民的奸臣左劈右砍,为大唐的命运杀出一条血路。到了后面的酒醒时分,一切归于平静,当郭子仪唱出“怕天心人意两难摹”时,观众皆为英雄扼腕长叹。
在戏曲舞台的方寸天地中,醉境如梦境一样,亦幻亦真,许许多多的角色在三杯两盏间钩沉过往,借酒来寻求精神慰藉,力图摆脱现实的桎梏,而求得内心的平和。不过,痛苦的醉和美丽的梦有着不同的神界。[5]醉境与梦境中所营造的理想世界不同的是,酒把角色带入幻境之后,在给予人勇气挣脱束缚的同时,也放大了人内心的痛楚。正是这种情感的挣扎在醉境中一直延续,使杨玉环在醉意正浓时依旧唱出“恼恨李三郎,竟自把奴撇”,使郭子仪唱出“不由人冷嗖嗖冲冠发竖,热烘烘气吭胸脯”。而他们酒醒之后,依旧要面对现实的无力与迷茫,杨玉环落得个“冷清清独自回宫去也”,郭子仪“看满地斜阳欲暮,到萧条客馆兀自意踌躇”。戏曲的生旦净丑,在唱念做打中演尽了人生百态,对于醉境之美的演绎,在于戏曲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情感传达,给观众带来独特的艺术享受和情感共鸣。通过精湛的表演技巧和细腻的情感表达,戏曲的醉境表演展现出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与深度。而在醉境之中,戏曲的美就绽放在那一抹唱得出又舞得起的愁滋味中。